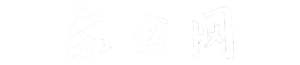内容简介
“被家放逐的一代人”
“不知道为什么,从佳木斯回到北京,人反而更怕冷了。”
“少平呀。”姜老蔫轻轻地唤起儿子,用手摩挲着一飞脑袋。“爸问你,你想回家吗?”
“我想回家。”一飞用力说。“可是我叫周一飞,您怎么糊涂啦?”
“对,姥爷糊涂了。姥爷不中用了。”
《如英》讲述南城姑娘姜如英,作为“六九届”知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。十年后她返城回京,与同为知青的周笑走到一起。同是各自家中长兄长姐的两人,此时却变成大家庭内部的异类和累赘。他们还要在错综不定的社会变迁中彼此支撑,共同面对外部世界的冷落与戏弄。小说以细腻温和的笔触,将如英周笑遭遇到的啼笑人生娓娓道来,更刻画出北京南城人横跨四十年的生活图景。
在家走失——《如英》创作谈
我是在白纸坊西街长大的,儿时在那里过着无所事事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日子。直到毕业找工作,我才从白纸坊西街离开,所以说我其实和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区别不大。这也造成了我的极度晚熟,无论是哪个方面,比如直到现在,我都认为无所事事并且能感觉到美好的日子,就是好日子。
我的小学在白纸坊西街偏东,我家住在西街偏西,每天一放学我们撒丫子就往家跑,这样才能赶上北京台播的《圣斗士星矢》。由于我家距离稍远,所以每次都赶不上开头五分钟,所以那五分钟里发生了什么,我是要等到第二天上学,在早课间听一个叫于博奇的家伙讲给我。由于我太想知道了,其他同学还总围过来插嘴,于博奇就更来劲了,那五分钟丫能讲两个课间,有的情节也跟我后面看的接不上,我就怀疑丫有瞎编的成分。直到有天我使出浑身力气往家跑,居然赶上了开篇动画,那可是我拼命跑出来的奖励,更重要的是于博奇知道后,他说你绝不可能赶上那五分钟,那个距离你是到不了家的!即便我说出那五分钟的情节,他也不信。但是对于我来说,最宝贵的是我可以不再经他讲述,独自去理解那五分钟了。而且如同是宿命一般的,现在的我仍然在这条路上,寻找那不被人承认,不被人理解的时间。
后来我的小学搬到法源寺附近一所研究院里,白纸坊的孩子要到当街坐公共汽车,坐到牛街南口。两站地之外的世界,对于孩子们可称得上遥远,好在我们不由自主地会结伴而行,你就不会觉得害怕。直到某天早上我跑到车站,发现车来了同学却不往上挤。我没来及多问,用力一蹿就上去了。当车门啪叽一关,我站在铁台阶上,看到同学们都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,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。很快,公交车到了牛街南口但没有停的意思,而是直接开到了下一站,我两条腿哆嗦起来。我带着哭腔甚至是祈求着问售票员,阿姨我们这是要去哪?她爱答不理地说,礼拜寺。礼拜寺,仅仅比牛街南口多出一站,我却觉得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了。
我两手攥紧书包背带,担惊受怕中双脚落地的一刻,眼前全是留长胡须、戴白色圆帽的人。他们五官立体,穿着对襟长衫,慢悠悠地聚集在街上,边走嘴里边念叨着什么,路两边还摆满我从没见过的糕点和器物。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,更不知道当天是回族的古尔邦节。只记得我仰着脑袋,独自站在街中间,好像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校服和书包,你能想象那个八岁的孩子有多绝望么。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国度,或者是原始部落,甚至连头顶的树都变得无比高大。我早已忘了学校的方向,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,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那些陌生人身后,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神秘香气。
当我意识到周围人的模样逐渐正常,天变得空旷,建筑物也跟着平庸起来,这才稍稍安心,我知道我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。我居然走回了学校,一进校门,大伙儿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把我围起来。于博奇说,我们以为你走丢了,我正要告诉老师你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当时还讲不出什么,无法告诉他我去哪了,看到了什么。但他说的没错,我确实走丢了,至于我是怎么回来的,为什么没有受到伤害,我把它归结为某种神迹。
那时我和表弟常去印钞厂里洗澡,俩人谁都不愿负责装毛巾肥皂的塑料筐。那是个浅绿色的塑料筐,有两个提手,拎久了还剌手。于是我们想出个绝妙的主意,一人提塑料筐的一个提手去印钞厂洗澡。那真是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场景,每到周末,两个秃小子一人攥着塑料筐的一边,以同样的步伐,并肩走在厂区里,大兵们见了都要多看几眼。由于表弟高,我个头矮,所以塑料筐里面的肥皂和毛巾总会掉出来,有次掉的是一大瓶蜂花洗发液,砸我脚面了,生疼。
带着深深的满足感,我们洗完澡,总要站在澡堂门口吹凉风。我告诉表弟,一人拿着一边塑料筐提手实在太丢人了,不如来时我提,回去你提。表弟说行。很快他发现,这样明显自己吃亏了,因为我们进厂时直奔澡堂,但是洗完出来,总要在厂区里乱窜。我们要爬树,要品尝花坛里的一串红花蕊,要在干涸的泳池里扮演圣斗士,或者在警卫连的兵营里,和那帮大兵摔跤。那也是我最神气的时候,而表弟无论干什么都要提着个装肥皂毛巾的塑料筐,跟在我左右。每当他也想爬树,也想玩双杠,或者从泳池跳台上往池底看的时候,我都会提醒他,你,别忘了拿好塑料筐。
他终于明白过味儿了,提出拿塑料筐的顺序应该变一变,但是我提醒他,别忘了谁是哥哥。有时我们玩的时间远比洗澡还要长,甚至天都黑了,他累得恨不能把塑料筐挂在脖子上,他有几次还故意扔到地上,踢了几脚。直到有一天,不仅来的时候是我提塑料筐,洗完澡我也主动拿筐,因为我带了个照相机出来。
暮色降临,厂区的地下管道在检修,我们不得不绕路。沿着一排迂曲的游廊,闻着被翻起的土地和松树混淆出的湿气,我们走到从未去过的印钞车间,那是真正印钞票的工作区。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慑力,不仅身体发冷,还有了尿意。走到高耸入云的虎皮色水塔下面,眼前已接近一片昏黑,只能听到凌乱的凉鞋声。
“给我看看照相机呗,让我按两下。”表弟说。“我帮你拿塑料筐。”
我说那可不行,虽然这是一部傻瓜相机,但是里面有着宝贵的交卷,按两下可贵了。又走了一段路后,我说天已经全黑了,如果想拍出人影,需要用闪光灯,我告诉他,电池可贵了。表弟不再说话,虽然他比我高,脾气也比我差,但是他沉默了。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,只好答应他等到走出厂区,我们就在大门口拍照,那里有很亮的灯。我们一人按一下,也不废电池。
可是我们越走越不认路,这才明白印钞厂太大了。我们能听到奇怪的鸟叫,还有那座标志性的德式钟楼,“咣咣当当”响个没完。
“八点了!”我们看着彼此,认真数着。
后来我们终于走出厂区,不过是朝着家的反方向,一直走到了大观园的南门。
“能拍照了吗?”表弟问我。我们确实需要庆祝一下,至少看到大马路了。
我仰起头,看着面前那块刻着“补天遗”的巨石,决定我们在这下面给对方拍一张。我正指挥表弟,怎么借助月光拍照片,却听到身后有人朝这边说话。
“你们这样可不行。”
是个大人,个子不高,但是个大人。我记得他的脸很白,眼窝深陷,双眉浓重,声音有些沙哑,而且还穿着一身黑衣。我和表弟早吓得不知该说什么。
“给我看看。”他伸手向我们要相机。看着他那副认真样,我真后悔为什么带相机出来。我觉得如果交给他,一定会被抢走。终于我还是从表弟手中拿回相机,交给了他,这时表弟紧紧贴住那人身边,我觉得他随时都能抢走。
然而那人看了看却乐了,他说你们没开镜头盖呢!表弟看向我,我还死死盯着我的相机。随后那人拿出纸条,用笔在上面写了一串文字。
“这是我的店,你们要是真想学摄影,来这里找我。”他对我们笑着。
当我确认他是把纸条和相机一起还回来后,我和表弟撒丫子就跑,我的凉鞋都跑到脚跟后面去了。
那几乎是我第一次与外部社会产生某种联系。虽然纸条早就扔了,可后来我总在想,他为什么要叫住我们,还让我们找他。直到长大以后,我还是会想,他应该知道我们太小,是不可能去找他学摄影吧。在某个夜晚,愿意给两个傻孩子写电话,愿意和他们聊聊摄影的人,可能他也在寻找自己的路吧。
我再一次走失,正是面对着家门口,那时我已经懂事了。但我还是弄不懂,自小便在姥姥家长大的我,怎么忽然进不去家门了。我看着姥姥在当街喊,听你妈的话,回你自己家去吧。我看着她的脸,却听不懂她的话。即使在我后来最无助的时候,我依然被拒之门外,但因为我的晚熟,对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自然一无所知。那似乎只是告诉我,你该长大了。印钞厂的保安把我撵出来,姥姥家的亲人把我撵出来,可是我没有长大。
当我搬离白纸坊,我举着那个傻瓜相机,对准自己家的每一个成员——床、沙发、书架、电视机、折叠桌和酱油瓶以及肥皂盒,我对准每一个角落,毫不吝惜地按下快门,并且全程打开了闪光灯(可想而知洗印出的照片和作案现场一样)。我想把这里的一切放大后印在心里,为此我甚至对着每一个房间跪下磕头。但我依然一次次地回来,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这条街上游荡,可是我没有长大。
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陋习——总要把白纸坊那一带走上几圈。我无数次经过和表弟打闹的巷子,经过槐树下姥姥家的窗前,经过富丽堂皇的印钞厂大门,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证明,我没有长大。至今我还是对无穷无尽的窗子感兴趣,对黄昏日暮时,映照着万家灯火的窗子感兴趣。那些如梦似幻的光线向我转达着,人们吃饭时在谈论着什么,或者为了什么感到忧愁。你可以从外面轻松走过一栋塔楼或是一片幽深的院落,但是几平米的房间内却是某人的整个世界。摆放在书桌上的物品次序,墙壁上的水渍和熏黑印记,茶几与扶手椅上的木纹,以及混淆在客厅里煤烟和潮气,窗子里的神秘世界永远吸引且阻止着我。
所以不断地了解和探索白纸坊,成为令我着迷的事。我读奥兹的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,读王鼎钧的《昨天的云》,看他们以赤子之心去写儿时的感受和梦境,去追溯父母辈那令人心碎的过去,他们平静又坦诚的文字令我也有了书写《如英》的念头,或者说令我意识到,从很久以前我就注定要写这本书了。对于白纸坊,对于父母的人生,对于那些家庭内部的不解之谜,我抱有着太久的幻想。于是在长达三年的访谈中,要以写作的名义与父母交流,我才知道他们是“六九届”知青,才真正知道我是知青的孩子,才知道他们对过去的苦难与不甘守口如瓶,造就了我的晚熟。于是,我便这样开启了一场回到过去的探秘之旅。
正是由于极度晚熟,我无法去相信自己的记忆和判断。我只能向他们反复追问过去的人与事,追问那些细节、动机和各种可能,我只能相信他们。直到母亲在我面前抽噎落泪,直到父亲沉默不语,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拨动的伤疤有多深。我的父母,或者说那一代人,从未真正地融入过这个社会环境。他们永远活在一种不合时宜的处境中,用尽全力也无法弄懂这一切,无法让自己被人接受,无法获得尊严。他们是被家放逐的一代人,被家诅咒的一代人。我在儿时看到的很多事情,很多选择,以及很多问题,随之也都有了答案。
于是我知道了我的晚熟、我的坚忍、我的愤世嫉俗,我的自私、我的狡猾、我的反复无常,这些是从哪而来的基因。我也知道了他们是我永远逃离不掉的底色。但他们与我不同,他们从未想过重回白纸坊,那里是他们的伤心地,或者说,家便是他们的伤心地。我的追问一度也激起他们对我的反问,令他们向我寻求答案。我仿佛看到他们始终也没有走出那片伤心地,仿佛看到的全是无望的答案。
即便如此,写《如英》的过程艰难却也幸福。那段日子里,我不仅可以回到八九十年代的白纸坊,还可以与从前身边的人重见。尤其是他们在一起时,不曾说过的话,我在这本书里帮他们说了。他们错过的人,我在书里让他们再度相逢。那些无法化解的误会与遗憾,我在书里替他们解释了。至于他们永远走失的那个家,我也在这本书里,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去。
当我听到这些伤害过我父母的人说,“那都是时代造成的错”,我为他们感到可悲。我觉得苦难与记忆不该分成三六九等,高低贵贱。也许你认为某些人一生的追求或者难以触碰的痛苦,是过于渺小甚至荒谬的,某些人的人生是简单到不可理喻的。但是谁又能界定,多大的苦难才是苦难,多复杂的人生,才叫人生呢。我认为即便是令孩子伤心的小事,即便是时代造就的无数重复的苦难,但它降临到个人头上,都不能因为渺小或者重复,就不值一提,就可以删除。
理解苦难,书写记忆,是不是一个小说家的必要素质?我不知道。我倒是看到太多人很会利用机会展示自己,在被许可后的台子上,奋力地舞弄着他的沉默,我为此感到羞耻。这样无聊的小说家,我也不懂写作的各类流派和主义,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小说家,我觉得这种纯粹的认识问题非常无聊。我可以什么都不是,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在家走失的孩子。
作者简介
常小琥,1984年生于北京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琴腔》《收山》等,中短篇小说见《当代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等刊,同时参与过多种影视剧本创作。曾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、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小说佳作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《上海文学》中篇小说奖、《北京文学》年度优秀作品奖等。